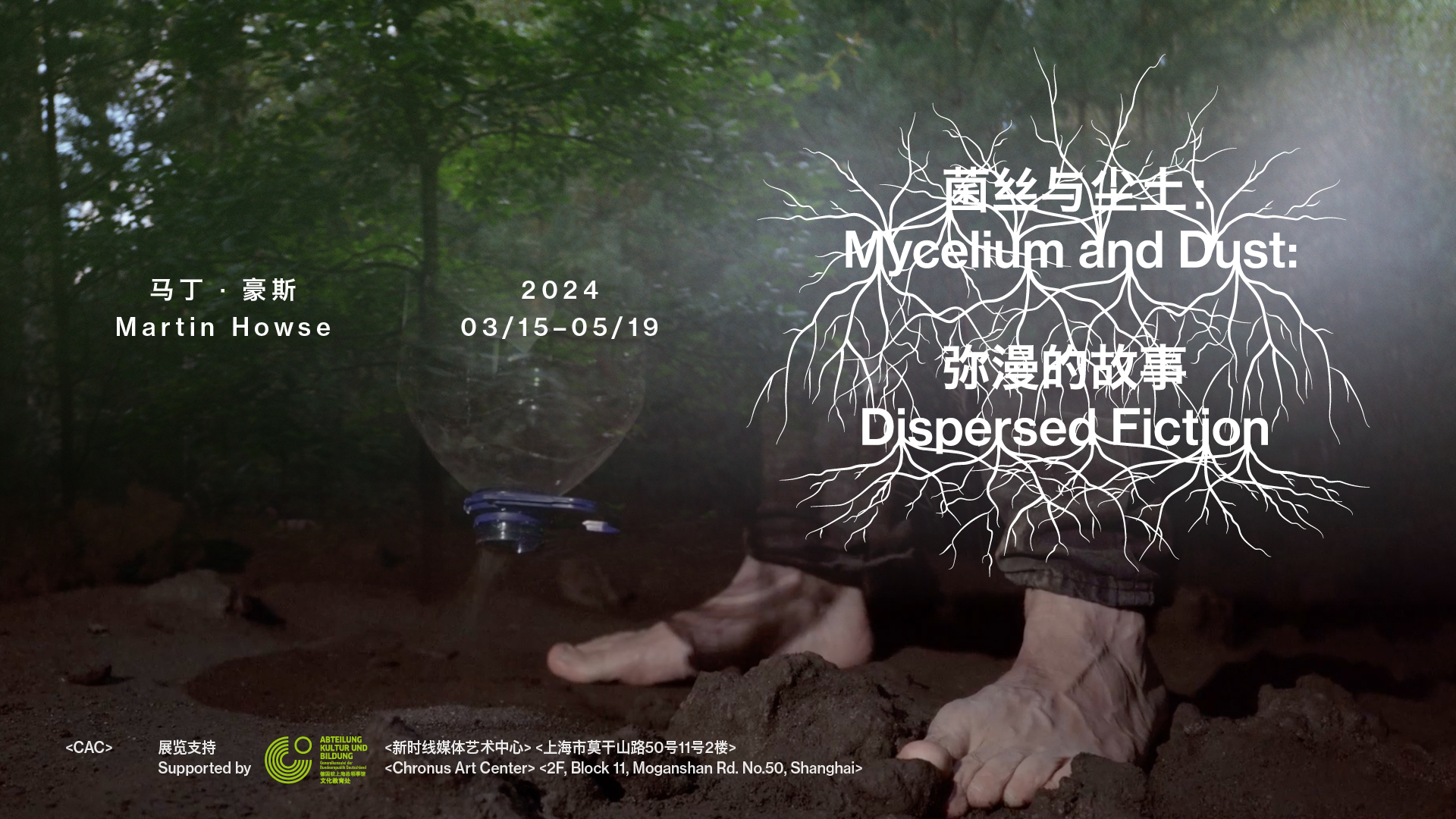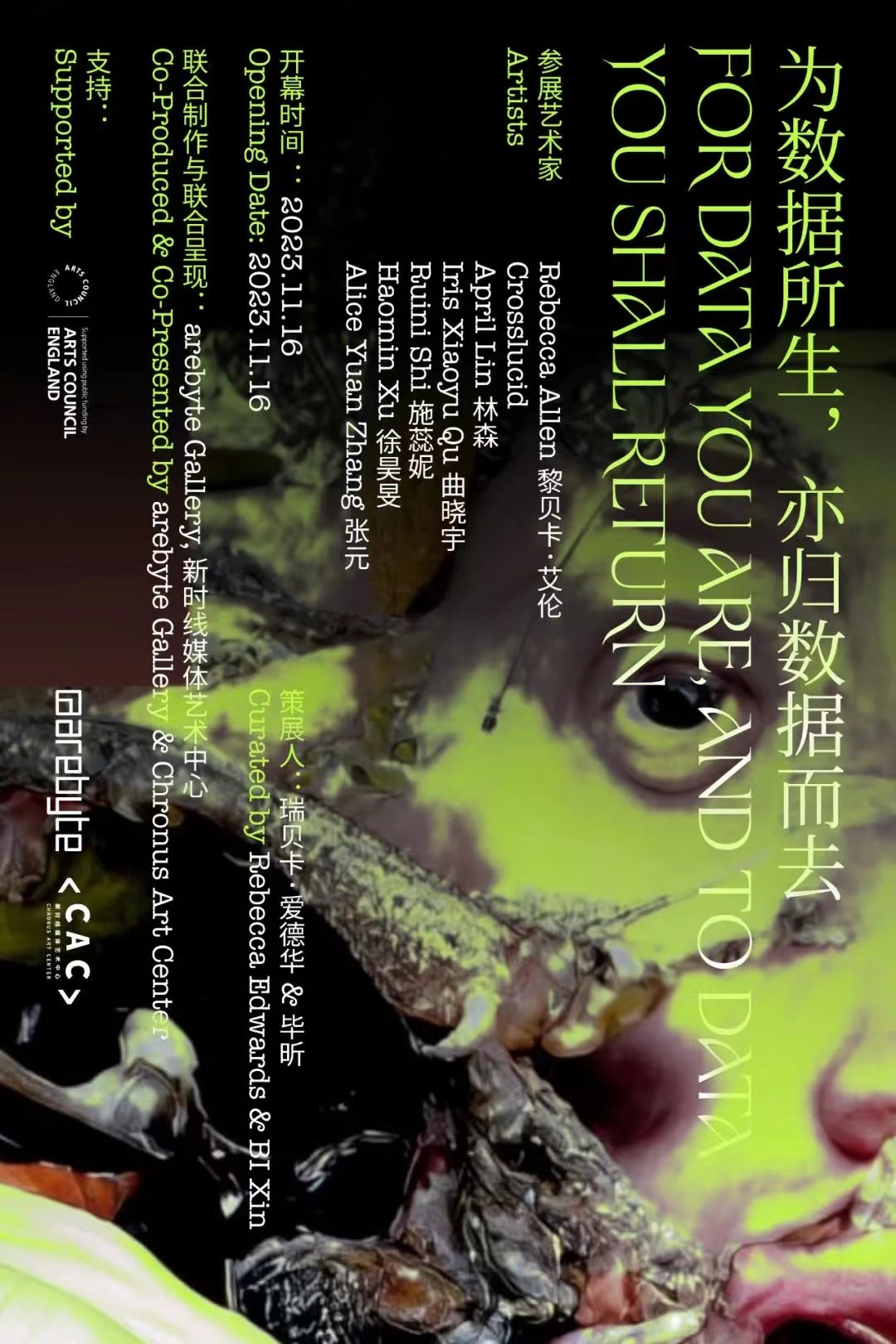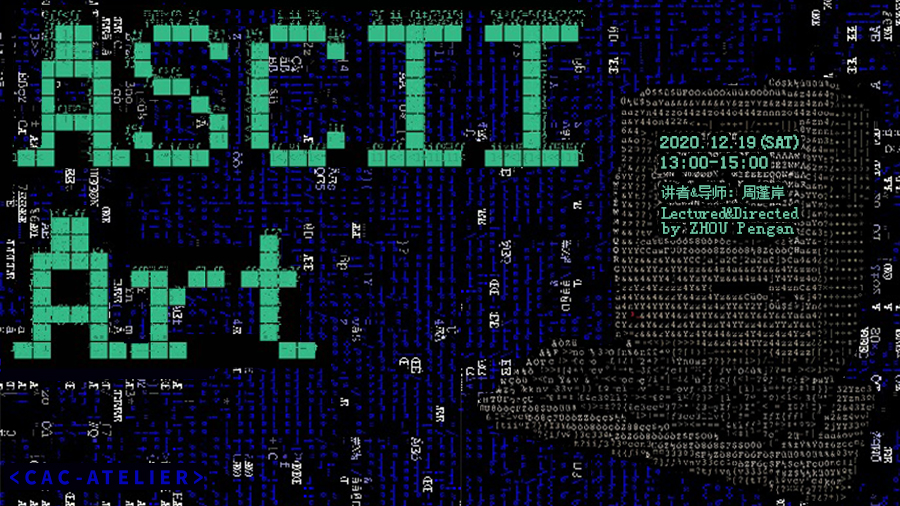姜宇辉
这肯定谈不上是一篇中立、客观的评述。我在这里只想按照自己的线索把手边的这几篇相当出色的论文串联在一起,就像水流一般,让它们产生一个共同的趋向与合力。这个趋向便是阿甘本在《论友爱》中给出的对当下时代的诊断,那就是装置与生命之间的争斗乃至厮杀;这个合力便是我们想在前卫的思想和艺术实验里面去探寻的一息尚存的希望,那就是反抗的契机乃至颠覆的可能。由此,Brian House的论文是相当突出的,因为它不仅明确提出了困境与问题,而更是通过转用Vito Acconci的经典作品来对当下进行一种颇有启示性的回应。援用他的精彩说法,关键问题恰恰在于,在一个人工智能看似无限增加和加速的年代,如何在数据网络之中真正成为一个individual而非dividual:二者的区分在于,后者只是捕获机器所操控的傀儡和砝码,而前者身上则尚有挣脱网络与保持距离的可能。在Acconci的原初描述之中,公共与私人(private)之间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分化;但在当下的时代,当私人领域亦已然被数据网络全面深入地渗透、监控和左右,那么又何以激活乃至释放其中尚存的“democratic potential”?House所复刻的Following Piece这件作品似乎给出了一个令人眼前一亮的思路:既然私人领域早已是一个千疮百孔的脆弱堡垒,那么在遍在的网络之中重新编织合力,似乎是一个可行的策略。然而,在这个方向上,我们必然会遇到德勒兹和瓜塔里的Rhizome网络理论和分子革命(molecular revolution)的构想,也必然会参考内格里和哈特关于诸众(multitude)之情动(affect)的天马行空的革命纲领。因此我们不出所料地读到了Jason Rhys Parry关于augmented ecology的论文。然而,所有这些源自《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的ecology理论在晚近以来皆越来越显示出强弩之末的疲态。如果说生态系统的本质就是多元、异质、开放的连接,那么这恰恰是我们时代的“症状”而非“希望”。借用Andrew Culp的说法,“过度连接(too many connections)”恰恰不是福音而是罪孽。既然如此,明智之举绝非去augment ecology(or rather ‘ecologies’),而反倒是中断连接、缩减网络、伪造消失(fake ‘disappearance’)。
就此而言,余下的几篇文章虽然在批判性方面不甚突出,但却仍然对House所提出的问题给出了不同方向的回应。Diego Gómez-Venegas和王洪喆的论文虽然令人遗憾地未涉及到当代艺术的实践,但却补充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历史性的视角。只不过,历史本身当然也是多面向的,Gómez-Venegas从技术史和媒介史所进行的考察、王洪喆从政治运动史所展开的挖掘自然会引申出迥异的结论:前者以“forgetting”为要点,将Kittler的媒介考古学与控制论的历史演变关联在一起,展现出重思人-机关系(“human-machine coupling”)的新颖视角;而后者虽然未重点关注技术本身,但却颇耐人寻味地展现出控制论等“西方科学思潮”在风云变幻的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的曲折命运。就此看来,其实“forgetting”倒是可以作为这两篇看似并不相关的文章的关联点。Gómez-Venegas的翔实历史考证固然出色,但却始终在一个核心要点之处含混不清、摇摆不定,那正是“forgetting”与“erasing”这两种操作的本质性差异。“forgetting”从根本上来说是主体自身的一种活动,从被动方面看它揭示的是人的认知的有限性,但从积极的方面看(比如尼采在《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中所言),它更体现出人类自身的那种创造性的抵抗力量。能忘记,想忘记,这不啻为人之为人的重要特征。用尼采的话来说,遗忘正是人的一种“健康”状态。但反过来说,我们不会用“forgetting”这样的词去描绘、界定机器的存储能力。确实,在机器的存储系统之中,信息的“erasable”也是一个关键特征,但这与作为主体的人的那种主动/被动的“forgetting”的能力之间所展现出的其实更是冲突而非一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forgetting”本可以作为一个抵抗的关键动力,而并非如Gómez-Venegas那般仅仅将其视作一个历史性的关联环节。而王洪喆对社会政治史的回溯梳理恰好给出了相当有力的回应:单纯从技术与媒介的历史脉络,是看不清“forgetting”的真相的。进行“forgetting”的操作的往往并非只是机器,而是更复杂的社会政治的力量,而当机器和政治这两方面的力量勾结在一起的时候,或许导向的是更为灰暗的前景。就此而言,Martinez de Carnero和Patrica de Vries的论文都深刻地阐释了当下艺术的状况,但却给出了两个全然不同的前景:前者的基调是乐观的,试图从前卫音乐的“improvisation”的手法中激发出新鲜的艺术实验的灵感;而后者则截然相反,试图以艺术的手法去展现大数据网络的“崇高(sublime)”式的恐惧(horror),进而趋向于一种末世般的悲壮。我自己更倾向于后者的立场,因为当希望不再掌握在我们手中之时,也许绝望反而是一种真正的、切实的抵抗。